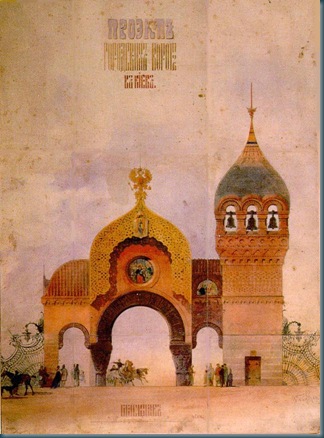有什麼事情會讓我同時想到草莓與咖哩雞這兩樣看似不相關的食物呢? 賣個關子, 讓我先回憶一段有甘有苦的往事吧! 猜到答案的請保密,不要講出來, 猜不到的也請不要像Harry一樣總是先翻到後面去看結局, 那多沒趣呀!
小時候, 我的母親會煮咖哩雞給我吃, 那湯汁淋在白飯上, 冒著騰騰的熱氣, 一直是我童年的回憶裡最懷念的景象之一. 我的母親在製作咖哩雞時所用的咖哩粉是會常變換的. 有時是市場賣的現成咖哩粉, 就在一般雜貨店裡幾小包幾小包地出售, 偶而母親會到中藥行配一下她要的口味, 後來也有從日本進口的咖哩塊, 口味有甜一點的, 帶一點辣的, 或比較辣的. 日本進口的咖哩塊以我現在的品味是覺得他們都有共同的一點膩, 當然那時還見不到道地的印度或東南亞的咖哩, 所以我當時沒吃過.
至於雞肉, 母親當然選用最棒的土雞肉, 雞腿與雞翅會剁成小塊後再加進去, 當然其他的雞肉也是. 吃咖哩飯時, 我習慣把飯與咖哩湯汁分開, 要吃時, 用湯匙舀一口飯, 放進湯汁裡一下下再舀出來吃, 料的部分就單獨吃. 我不喜歡像父親一樣把一切和在一起的那種條理不清的方式.
自小到大, 我是不必動刀與鍋勺的, 就是所謂的手不動三寶, 連煎蛋都要母親弄. 我是這樣地被寵溺大的. 直到出國後.
我帶在身上的錢並不多, 那是家人借貸來的. 在紐約, 假如是外食, 一般是非常貴的. 當時, 學校的可樂一瓶要價0.75USD, 一個麥當勞漢堡要價3.5USD. 雖說我以前在台灣是照吃不誤, 但後來家中的經濟狀況下滑, 3.5USD的漢堡我是無論如何也吃不下去.
所以自己準備吃的是最省錢的做法. 在紐約, 超級市場的東西當然貴過外州, 不過一般說來不會比台灣貴上太多. 打折時, 買一箱 Coke, 平均一罐不到0.2USD, 至於雞腿, 一大盒, 12~18支可能只要2.99USD. 一加侖牛奶也就是1.99~2.49USD. 到美國, 在吃了幾個星期的吐司夾火腿與起士後, 我終於忍不住了. 我回想到母親煮咖哩雞的過程, 覺得並不難, 周末, 我跟房東借了一個大鍋子, 決定自己來煮煮看. 我上超級市場買了一盒微辣的佛蒙特咖哩塊, 一盒18支的雞腿, 一些蔬菜, 再加上蘋果. 為了得到較好的結果, 我買了一包貴一點點的黃標國寶米. 最後在離開前發現草莓在大打折, 一大盒才3.99USD, 比台灣便宜上好幾倍, 所以順便帶上一盒, 準備回到住處大顯身手.
我首先煮了一大鍋水, 把雞腿燙了一下, 然後倒了一大堆油到炒菜鍋裡, 把清洗後瀝乾的雞腿放進去後將表面煎成淺咖啡色, 然後在大鍋子裡把水煮開, 放進切好的蔬菜與蘋果, 等個三分鐘後接著把雞腿放進去, 再按照佛蒙特的指示, 把一半的咖哩塊另外放進水裡稀釋均勻, 然後再倒進鍋子裡一起攪拌. 我把火關小, 讓湯汁微微冒著氣泡, 同時也輕輕地攪拌以免鍋底焦掉, 所有該注意的我都小心的做到了.
最後我倒進一點點鮮奶, 然後心血來潮地放進十幾顆洗好去蒂切半的新鮮草莓.
香噴噴的咖哩雞好了, 這咖哩雞塊所煮出來的咖哩雞呈現迷人的金黃色. 而在此之前, 我已經預先煮好了而且放著保溫約15分鐘的國寶米飯了, 我的內外鍋水量放得很剛好, 這是大同電鍋煮出來的有一點黏又不會太黏的白米飯, 也很像是在家裡看到的母親煮出來的白米飯. 我照著在台灣時吃咖哩飯的習慣, 把飯與湯汁分開來吃的方式, 一個碗裝咖理雞, 一個碗裝著白飯. 我在桌子的對面也擺了同樣的東西, 包括餐具, 飯以及最重要的咖裡雞. 然後一個人, 在飯廳享受著這不輸母親煮的咖哩雞, 而且因為草莓的特殊酸味, 這咖裡透著一付清新, 我一邊自豪, 一邊感傷, 一邊眼淚就不自禁地撲簌地掉了下來. 吃完我自己這份, 伸手把對面的那份也拿過來吃個精光.
洗完碗, 我一邊念書一邊等這咖哩雞涼了後, 就直接把它放進冰箱裡屬於我的那一格.
這一鍋咖哩花了我不到10USD, 我的如意算盤是一天吃一點, 大概可以吃上個十天, 這樣我一天的餐費就不到1USD, 即使加上早餐的吐司火腿與牛奶, 也才超過1USD一點點而已. 這樣我就可以把一個月在吃的方面的花費控制在約40USD. 加上房租160USD以及車錢, 一個月的基本花費不到250USD, 假如不打電話的話. 而事實上, 我也沒什麼電話要打, 通常也就是母親與家姊從台灣打電話給我的機會居多.
不過, 事情接下來的發展就不在天真以及過去不懂生活的我的控制之下了, 這一鍋美味的咖哩雞像是人老珠黃的糟糠妻,只是它變老的速度快了一點, 心上的朱砂痣沒幾天就成了牆上的蚊子血, 等到第參次我拿出它來加熱時, 所有的雞腿肉像是秋日的花瓣一片片地離開花梗掉落一樣, 一下子就從骨頭上分離了開來, 平均地散在整鍋咖哩裡面, 等到再下一次時, 雞腿肉從肉塊變成肉絲, 再下一次時, 肉絲就幾乎被分解成肉屑了, 還好那時奈米技術還不發達, 否則這些肉屑恐怕要被分解成奈米肉粉了.
至於顏色, 那更是糟透了, 金黃色變成土黃色, 土黃色變成咖啡色, 再下去我就不忍說了. 夏日裡閃著金光的玫瑰, 在入秋時化為塵土, 在這裡你不得不承認造物主很喜歡隨時隨地拿這碼子事來跟我們開玩笑, 連煮飯吃飯這檔子事也不例外.
倒掉嘛!我想. 照我以前的公子哥的習性是肯定會這麼做的. 不過我沒有, 因為想到那是花了我10USD以及一個小時的辛勞煮出來的. 我決定照原定計劃, 在接下來的七天裡, 一天天讓鍋子裡的東西減少. 每天, 我面對新鮮與香噴噴的米飯, 加上糞土色的咖哩雞肉屑湯汁, 把視覺與口感徹底從我的感官裏暫時剔除, 我一口口的吞嚥過程裡, 還是可以確實無誤地感受到它的香味, 甜味, 辣味以及可口的酸味. 最值得慶幸的是那草莓真是又大又好吃, 那是餐後我所能得到的惟一的獎賞.
當最後一天到來, 我清空了那一鍋咖裡雞時, 我的房東, 年邁眼睛不太看得見的房東的母親, 來自大陸與香港的兩位室友, 用無比欽佩的眼神看著我, 因為他們到後來用肉眼都分不清楚那是什麼料理了, 假如它還可以被稱為料理的話, 而一個來自號稱富裕的台灣的學生竟然可以把它吃完. 不簡單, 不容易, 苦了你了, 他們說.
那一天, 我並沒有如同第一天吃咖哩雞時掉下眼淚來, 我的心裡反而覺得平靜又平常無比, 一點也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 我告訴自己, 接下來的日子比這還苦還難的事還多得很呢! 事實也證明, 我在紐約的前兩年裡, 要遇到的難過的事還真的不少呢!
當然, 接下來的七年裡, 我沒有再吃過一次咖哩雞, 一直到回了台灣後在某一次與朋友的聚餐裡才再次開啟我吃咖哩雞之門, 不過隨著我發願不吃肉之後, 我就又沒機會吃咖哩雞了, 當然, 不帶肉的咖哩料理我現在還是常吃的. 過去的那一段經驗並沒能把我對咖哩的喜愛消滅, 一部分原因是咖哩真的本身就是一樣可口的料理, 但是更多的理由是我從咖哩料理裡可以感受到母親對我們的愛, 那是我這一生最最幸福的事了.
另外是要提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也就是隨著這次的經驗, 我那時決定要好好學一下自己煮東西吃, 當然了, 我也體會到自己當時有多笨, 那時, 我應該把一鍋咖哩雞分裝成小包, 每次要吃時拿出一包來解凍加熱就成了. 也因為我有心學好煮菜, 那一段紐約求學的時間裡, 我的煮菜技術在同學裡大概就只輸給一兩位女同學而已. 這是後話.
.
.
.
好吧! 什麼有趣的事情會讓我回想到這段往事呢? 當然是有關咖哩雞與草莓的事情囉! 喔! 假如你年未過18, 那麼請自動跳過下面的文字, 免得人家說我為老不尊. 故事到這裡應該是夠精采到可以當作完美的結局的囉!
.
.
.
好吧! 你確定你是超過18歲的了嗎!
.
.
.
也因為我最一剛開始的房東與室友分別來自香港與上海, 這兩個地方的人習慣將脖子上的情人的吻痕戲稱為草莓或咖哩雞, 至於哪一個是香港的慣用語, 哪一個又是上海的慣用辭我是記不得了.
有一天, 我的一個學生來跟我討論論文. 喔! 他當然是超過18歲了, 事實上他已經是個研究生, 所以應該有23歲了. 我們討論完論文後, 照例我會關心一下學生的生活狀況, 就在這時, 我看到他的脖子上有好幾個吻痕, 我不自禁地想起這段咖哩雞與草莓的往事, 一下子, 所有跟這鍋咖哩雞有關的酸甜苦辣滋味都湧了上來, 我的視線也指向遙遠的, 十多年前的學生生活. 時間也就似停止了的一般, 停在我25歲那年, 初到紐約, 住在A train的Grand Ave.的那一段日子, 當然還有那一鍋糞土色的, 我的料理初體驗.
一時之間, 我忘了要把我的視線的延伸線移開到學生的脖子以外的地方, 而且我的臉上大概是泛著異樣的光芒吧! 這表情我猜大概是忽而苦笑, 忽而憂鬱, 忽而哀傷, 忽而釋懷吧! 因此我的學生大概以為我是在注視著他的咖哩雞草莓, 開口打斷我的思緒, 像是非常不好意思而扭捏地向我解釋說那是他的女朋友為了作弄他所故意吸吻的. 我回過神來, 停了一下才聽懂他的話, 我笑著說, 沒關係啦, 年輕人嘛! 好玩就好, 不過要小心, 不要弄出麻煩事情來, 也一定要好好對人家負責喔!
我語帶玩笑地說著. 學生一下子脹紅了臉連聲說是後趕緊告退.其實我另一個的意思是:
年輕人嘛! 煮菜好玩, 但是不要把菜弄得奇奇怪怪就好, 而即使菜不好吃, 終究是自己煮的, 還是要負責任的吃完它喔!
對了, 今天忘了介紹唱片了. 就這張吧!

帕爾曼跟一堆朋友弄的Jazz. 很發燒, 好聽又輕鬆, 至於它跟草莓咖哩雞的關係我是找不出來的啦!